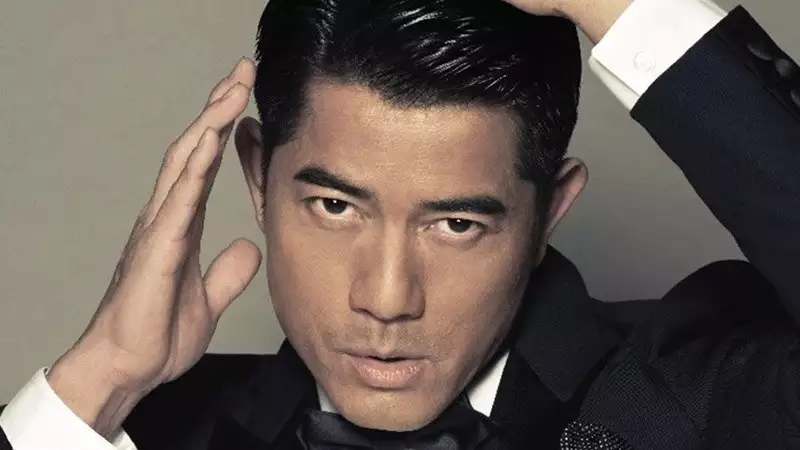电影中女性角色的成长(电影中女性角色之间没
今天是法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编剧、导演、社会评论家玛格丽特·杜拉斯诞辰战争电影110周年。我们一同来回顾杜拉斯导演的两部最富盛名的电影《印度之歌》和《巴克斯泰尔,薇拉·巴克斯泰尔》。《印度之歌》公映于1975年,在这个讲述注定陨灭的激情故事中,杜拉斯以反自然主义的美学风格、年代战争电影混乱的布景以及矢志不渝的浪漫主义姿态同传统电影决裂。她对电影声音的激进探索至今仍难以超越,最标志性的手法便是将咒语一般的对话安插在精美绚丽的置景中。
两年后,杜拉斯拍出了《巴克斯泰尔,薇拉·巴克斯泰尔》战争电影,影片女主是欧洲艺术电影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星之一——著名女性主义活动家,1975年的杰作《让娜·迪尔曼》的女主角德菲因·塞里格——杜拉斯把最珍贵的台词都给了这个角色,包括她经常用来说明女性如何从沉默寡言战争电影中生出力量的一句话:“女巫也是这样来的。在中世纪,男人们都在外打仗,参与十字军东征,乡村妇女们被抛下,独自一人,与世隔绝,整月整月地呆在森林小屋里……正是在这种孤独中,她们开始同树木、植物交谈,从自然战争电影中创生智慧。但她们被当作女巫,被烧死。”这句话出自儒勒·米什1862年的史学著作《女巫》,杜拉斯在后面加上了半句,“其中有一位,叫薇拉·巴克斯泰尔。”塞里格这段关于女性被抑止语言的旁白,让这个人物变成战争电影了杜拉斯的代言人。
相关文章:玛格丽特·杜拉斯:我从不做梦,这就是为什么我写作……
《印度之歌》
在杜拉斯的笼罩下
《巴克斯泰尔,薇拉·巴克斯泰尔》
译者:热带幽灵
设计学在读,电影热爱者
原作者:Ivone Ma战争电影rgulies
原文链接:
https://www.criterion.com/current/posts/8082-india-song-and-baxter-vera-baxter-in-the-th战争电影rall-of-duras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的《印度之歌》(India Song, 1975)是一首催人入眠的爱之歌,是影史上最曼妙的电影之一,杜拉斯在其中沿用了她拿战争电影手的复调写作手法。影片有一个无边无际的中心场景——加尔各答的法国大使招待会。舞会上,四个身着切瑞蒂1881西装的男人徘徊在一个魅惑的红发女人(德菲因·塞里格饰)身边,同她共舞。
《印度之歌》剧照
片中一直战争电影有一些不在场的观众,有时候替角色说台词,有时候又在议论角色,就像偷偷穿越到了这个传说中的国度,我们在看得入迷时也会加入其中。主场景是一个镜厅,伦巴舞曲和刺耳的喊叫不绝于耳,无论影片落幕多久,这个镜厅和战争电影其中的幽灵都一直萦绕着我们。
《印度之歌》公映于1975年,在这个讲述注定陨灭的激情的故事中,杜拉斯以反自然主义的美学风格、年代混乱的布景以及矢志不渝的浪漫主义姿态同传统电影决裂。她的作品里有一种迷人又战争电影简洁的戏剧特质,和同时期的雅克·里维特(Jacques Rivette)、曼努埃尔·德·奥利维拉(Manoel de Oliveira)、让-马里·斯特劳布(Jean-Marie Straub)、达尼战争电影埃尔·于伊耶(Danièle Huillet)一样,她全然不顾惯常的类型界限。她对电影声音的激进探索至今仍难以超越,最标志性的手法便是将咒语一般的对话安插在精美绚丽的置景中。
《印度之歌》剧照
直到《印度战争电影之歌》1975年在戛纳非竞赛单元首映时,杜拉斯已经当了快十年的导演。作为已经成名的小说家和剧作家,她选择执起导筒的部分原因是,对其他导演改编她的戏剧和小说感到失望:比如雷内·克莱芒(René Clém战争电影ent)版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This Angry Age, 1957),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的《琴声如诉》(Seven Days ... Seven Nights, 1960)战争电影,托尼·理查森(Tony Richardson)的《直布罗陀水手》(The Sailor from Gibraltar , 1967)等等。《印度之歌》海报
1967年,杜拉斯和保罗·塞班(Paul S战争电影eban)一起执导了《音乐》(La Musica, 1967),影片根据她写的一出短剧改编,从那时起,一直到在观念上极为挑衅的《孩子们》(The Children, 1985)为止,杜拉斯拍了长短不一战争电影的十九部电影,无一不在颠覆我们习以为常的惯例。法国作家、批评家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关注到杜拉斯勇于越界的品质,说她独立执导的第一部长片《毁灭,她说》(Destroy, S战争电影he Said, 1969)身处“书籍与电影之间”。
杜拉斯用抛弃观众的方式去捣毁电影的写实主义天职。她这些纯粹的作品敢于引导人少去看,多去听。虽然关注文字的节奏和音调是她更早期作品的标志性特征,但还是战争电影在 “印度系列”电影中——《恒河女》(Woman of the Ganges, 1974)《印度之歌》《她在威尼斯时的名字在荒凉的加尔各答》(Her Venetian Name in Deserted战争电影 Calcutta, 1976)——文字的存在最引人注目。
《卡车》(The Truck, 1977)是一部公路电影,但外景很少,主要拍的是杜拉斯和热拉尔·德帕迪约(Gérard Depardieu)在战争电影镜头前朗读。她一直试图打破电影对视觉的依赖,让这一媒介成为人们动情倾听的场所。让-吕克·戈达尔在《各自逃生》(Every Man for Himself, 1980)中致敬杜拉斯说:“每当你看见卡车驶战争电影过,那是女人的话语路过。”
《卡车》剧照
书面和口头文字将人的内在思想投射出来,电影则帮助杜拉斯将这种投射成倍地扩大。通过循次而进的朗诵,经验之流被缓缓倾倒出来,在某处汇集,她把这个汇聚之处叫做“内在的阴战争电影影”(internal shadow)。就像接连而至的海浪一样,她的文字相互碰撞,相互消解,把世间万象融合在一起。
早在她为阿伦·雷乃(Alain Resnais)写《广岛之恋》(Hiroshima M战争电影on Amour, 1959)的剧本时,她看重意合的风格就在开头的蒙太奇段落中有所体现。抽象的身体抱在一起,她写道,“被灰烬,雨水,露水,或是汗水浸湿,无论哪一种都好”——这些闪烁着激情的词语将电影画战争电影面与社会公众、与原子弹爆炸联系起来。在肌肤之上,这些结晶体从个人和历史两个维度凝结了雷乃和杜拉斯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灾难,以及灾难过后潜在的遗忘。
《广岛之恋》剧照
雷乃在拍《夜与雾》(Night and战争电影 Fog, 1956)时和历史学家奥尔加·沃姆瑟(Olga Wormser)一起工作过,后者向雷乃引荐了杜拉斯,这说明杜拉斯无论在战前还是战后都是法国颇具声望的政治参与型知识分子。
她1914年出生于西战争电影贡,西贡当时是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她在中南半岛很多地方辗转居住过,先是跟着父母,然后是殖民地的老师,父亲去世后又跟母亲在一起。1930年代初杜拉斯回到法国,在那学习了法律和政治学,然后去了殖民地间信战争电影息和档案部(the Intercolonial Service of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工作。1943年她发表了首部小说,同年参加了抵抗运动。
杜拉斯照片
194战争电影5年,她的第一任丈夫罗贝尔·安泰尔姆(Robert Antelme,法国作家,1939年与杜拉斯结婚,1944年因参加抵抗运动被迫离开法国,被捕进入纳粹德国达豪集中营。代表作有《人种》)从达豪集中营回战争电影来时被折磨得命悬一线,她一直照顾他直至康复。四十年后她出版的《战争》(The War: A Memoir)一书详细描写了这段经历。
战后,杜拉斯在巴黎圣伯努瓦大街的家成了人们思想碰撞的辩论场,离经叛道的战争电影知识分子和反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者常常出入其间。她参与创立了万国出版社(la Cité Universelle),推广了包括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的《德意志零年》和罗贝尔·安泰尔姆的《人种战争电影》(The Human Race, 1947)在内的诸多开创性作品。她还是十分锋利的记者和评论者,同时为主流报纸和专业性刊物写稿;
杜拉斯照片
她积极投身反阿尔及利亚战争运动,参与签署《121宣言》(19战争电影60年9月由121名法国知识分子签署并发表的反战宣言,代表法国知识界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回应。宣言的主要作者之一是前文提到的莫里斯·布朗肖,其他签署者还有罗贝尔·安泰尔姆、阿兰-罗伯·格里耶、让-保罗·战争电影萨特、弗朗索瓦·特吕弗等),还参加了1968年的运动。1970年代,她探讨女性问题,但从不接受“女权主义者”的标签。后来,杜拉斯坚持认为,她总是“在坎普的意义上去写作,就算单词本身不明晰。”
杜拉斯“印战争电影度系列”中的人物在几部作品间循环出场,这些人物的出处刚好构成两组三联画:小说《劳儿之劫》(The Ravishing of Lol Stein, 1964)《副领事》(The Vice-Consul,战争电影 1966)《爱》(L’amour, 1971),以及电影《恒河女》《印度之歌》《她在威尼斯时的名字在荒凉的加尔各答》。此外,书籍版《恒河女》、伦敦国家剧院委托改编的舞台剧版《印度之歌》、电台版的《印战争电影度之歌》以及电台版《副领事》也构成对这个循环的补充。每个版本都是对原作者有关记忆、欲望与毁灭探讨的深化。
杜拉斯照片
杜拉斯强迫性地一再回到她无法舍离的地点和人物中去,这确证了她对法属印度支那有着无法自拔战争电影的迷恋。她醉心于的第一个对象是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杜拉斯“记得”她是永隆市领事的妻子,经常在使馆区出没,面无血色。一个无法忍受印度的女人,以及一个为爱自杀的年轻男人,这两桩传闻勾起杜拉斯躁动青春中战争电影的无限遐想。在整个“印度系列”里,杜拉斯笔下的斯特雷泰尔都处在致命的爱中,同时透着殖民地衰落腐坏的情绪。
《印度之歌》剧照
斯特雷泰尔首次正式出场是在小说《劳儿之劫》中,一场舞会结束时,她身着一袭黑色绢纱战争电影裙出现,把劳儿的未婚夫麦克·理查逊迷得神魂颠倒,最后二人抛下劳儿离开了舞厅。劳儿失魂落魄地凝望着他们,凝望着这两人对彼此的深情目光。杜拉斯赋予这种极端的、自我摧毁的暴力以神话色彩,并且在整个“印度系列战争电影”中一次又一次地回顾这样的时刻。有许多场景——《劳儿之劫》中亮灯的旅馆窗户,《副领事》中空荡荡的网球场,《印度之歌》中大使府邸的客厅——好像都只是为了吸引情人的目光而存在,那些不被接纳的、如饥似渴的情战争电影人。
纵览“印度系列”中的所有作品,《印度之歌》是把这种充满禁忌感的空间设定得最出色的一部。影片彻底将声画分离,再造出一种反常的感官愉悦。片中只有一个主画面,镜头从典雅的镜厅中飘忽摇过,让我们目不暇接。战争电影我们被画外音包裹,不自觉地代入其中,观看一个无法存在于自然中的场景。
杜拉斯说这些声音构成了一个“围绕着凝滞画面的回声场……静态的画面把回声场固定住,防止这些声音四散漂流”。演员们从不开口,这种交流挑逗战争电影着我们对完整形式的欲求,挑逗着我们让台词和身体动作同步的渴望。有时候,导演在剪辑时会让已经离开画面的角色继续在画外说话。用她的话来说,除了“可见的”对话,我们还能听到被“埋藏”的或“失去”的声音,来自战争电影舞会上的旁观者。
《印度之歌》剧照
两个年轻女子的声音“甜蜜而略带疯狂”,对应杜拉斯说的“遗忘的记忆”。她们着了魔似的想要唤醒《印度之歌》的故事。招待会上的宾客说话用的是现在时态:“他们正跳舞”;但其他人战争电影(杜拉斯第二任丈夫迪奥尼斯·马斯科洛、杜拉斯、维维亚娜·福雷斯特)用的却是过去时态,用来指称过去发生的事件:“他们会(would)在晚上跳舞”。
在这种呼唤-回应的结构中,对话被悬置成为疑问,人们像是被战争电影困在一个回声震荡的密室,当下总是充满了困扰。音轨上循环的音乐——卡洛斯·达雷西欧(Carlos d’Alessio)创作的“印度之歌蓝调”(India Song Blues),以及贝多芬第十四迪亚贝利战争电影变奏曲——似乎并未与过去或现在产生关联。存在与缺席之间进行着复杂的互动,这些音乐就像是它们背后伤感的衬布。
在《印度之歌札记》(Notes on India Song)中杜拉斯提到,“钢琴上有死去的女人战争电影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的照片,还有她记忆中的玫瑰和香炉——这个祭坛……应该……让人怀疑(接待会)及其周围发生的一切”。同样,大厅的镜子也起到一个类似黑洞的作用,场景交替笼罩在光亮和黑暗下,睡眠、倦怠和战争电影死亡混作一团。导演反复让镜头摇过物品,比如假发、红裙子、黑袍,使斯特雷泰尔显得死气沉沉,即便她在下一个镜头中容光焕发、翩翩起舞。
为了强化这种效应,杜拉斯在拍摄过程中反复播放《印度之歌》的对白录音,演员战争电影一边听自己说的话一边听导演指示,难免心烦意乱,心不在焉,从而更加克制自我表达。此外,杜拉斯放慢了对白的节奏,使其不带任何语调,形成一种朗读“之前演好的东西”的听感。
在《玛格丽特·杜拉斯拍电影》(Mar战争电影guerite Duras tourne un film)一书收录的一篇访谈中,演员马修·加里瑞(Mathieu Carrière)仔细回忆了杜拉斯的置景:“在摆放好静物之后,她会让烟从香炉中飘出来,战争电影加强景深的不对称性,彰显出画面的微小变化。”有一个静默到可怕的场景,斯特雷泰尔和几个情人坐在威尔士亲王旅馆喝酒,提及这个场景的拍摄时,他回忆道:“她提出这样的挑战,演员病态地警觉起来:‘我会让你瘫痪,战争电影如果你死在印度的法国大使馆,那就试试抽根烟’.”
杜拉斯没有用群众演员,这赋予了影片戏剧化的诗性。她把影片提纯到只剩五个可见的主要人物和几个固定的地点,这种紧凑的设置就像一台离心机,高速旋转,加固意义。战争电影其中的三个男人——麦克·理查逊(克罗德·曼饰),年轻的随从(马修·加里瑞饰),年轻的客人(狄迪尔·弗拉蒙饰)——都将是或者已经是斯特雷泰尔的情人。
杜拉斯照片
这个亲密的圈子把两个人拒之门外:副领事(迈克战争电影尔·朗斯代尔饰)和女乞丐,这两个人物是一组,女乞丐一直喋喋不休,我们能听到她的笑声,但她的台词没有翻译,所以无从知晓其中内涵。他们俩被放逐在领事馆的边缘,各自代表一种对殖民主义之荒谬的潜在回应:两人都战争电影疯了——女乞丐一无所知地流浪,副领事则陷入无所不知后的绝望。两人都在追寻加尔各答的白人女子斯特雷泰尔,联系她、玷污她。
杜拉斯并不在乎名称上的精确,她提醒观众,她是“在音律的层面使用印度城镇名、河流名、战争电影州名和海洋名的”。然而,即使她赋予文字以纯粹诗意的共鸣,但她还是化用加尔各答和拉合尔(如同《广岛之恋》中的广岛和纳韦尔)这两个地名,作为这个帝国虚幻的、摇摇欲坠的暗语——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代表加尔战争电影各答,副领事代表拉合尔。
《印度之歌》对一个杜拉斯式的漫长疑问作出了回答:如何把一个关于爱和欲望的故事,镶嵌在一出关于世界末日的悲剧中?答案是,叙事摇摆于以下两者之间,一是白人之间看似不重要的、由渴望到战争电影厌倦的反复循环,二是殖民地疯狂秩序背后难以遏制的骚动。事实上,一旦这种和鸣主宰整部《印度之歌》,影片的悲剧感就能以一种潜在的方式隐透出来,客气的交谈化解了副领事大喊大叫斯特雷泰尔名字的尴尬,就像片中的战争电影窃窃私语:“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应该都在尖叫。为什么?我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说……”。
达雷西欧的配乐也有类似的消减情感功能。从探戈到华尔兹、拉格泰姆、布鲁斯、伦巴,正如杜拉斯所言,“尽管有事发生,比如副领战争电影事的尖叫”,音乐却总是很轻盈地喷涌而出。
杜拉斯最终把这出骚动不安的戏剧定位在一个更宽广的历史背景板中,给了斯特雷泰尔之死一个确切的日期。杜拉斯和维维亚娜·福雷斯特清甜的声音交替响起,诉说着三十年代命定战争电影的溃败:“正值一个九月的傍晚,夏季风拂过群岛,那是1937年。中国战火未停,上海刚被炮火轰炸,日军一直向前侵犯。西班牙也仍在打仗,共和国遭血洗。纽伦堡会议刚刚召开。”
杜拉斯下一部电影《她在威尼斯时的名战争电影字在荒凉的加尔各答》的反电影程度达到了整个印度系列的巅峰,并且终于让她摆脱了斯特雷泰尔这个人物。这部影片沿用了《印度之歌》的整个原声,配合的画面是里里外外一片破落的罗斯柴尔德城堡,这个地方在巴黎市郊,战争电影《印度之歌》的大部分镜头是在那拍的,声音回荡在荒芜之地。
《她在威尼斯时的名字在荒凉的加尔各答》海报
《她在威尼斯时的名字在荒凉的加尔各答》拍摄期间,杜拉斯和她的摄影师布鲁诺·努坦(Bruno Nuytt战争电影en,也是《印度之歌》的摄影)
并肩而行,把录音带里播放的声音配上努坦拍摄的推拉镜头画面。这座位于布洛涅森林的宫殿二战时曾是纳粹驻地,之后再也不属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导演选择它作为《印度之歌》的取景地。这战争电影个地方是空壳外的空壳,凝固在层叠的历史中,杜拉斯选择在这里作最后的哀悼——她说,在一个“荒芜”的地方,“诉说世界的尽头”。
《巴克斯泰尔,薇拉·巴克斯泰尔》剧照
在拍完与印度有关的作品、进行完《卡车》对电战争电影影声音的激进实验后,杜拉斯通过《巴克斯泰尔,薇拉·巴克斯泰尔》(Baxter, Vera Baxter, 1977)回归到她在《娜妲莉·葛兰吉》(Nathalie Granger, 1972)中就开始战争电影探索的题材:一个由女性组成的宇宙,那里被沉默笼罩,有一座亦安全亦危险的房屋,外面和森林大海相接,在冬日苍白光线的映衬下略显怪异。
这两部电影都弥漫着一种精致、沉静的不详之感,即便《娜妲莉·葛兰吉》中充斥战争电影着的由女巫、黑猫等意象营造出的神秘感在《巴克斯泰尔,薇拉·巴克斯泰尔》里被稀释了,《薇》的命题更加抽象,残酷地反映资产阶级的乖顺和淫乱,或者用作者的话来说,是“一个地狱般的轮回,让她往返穿梭在对孩子的战争电影爱与对婚姻的责任中”。
《巴克斯泰尔,薇拉·巴克斯泰尔》海报
《巴克斯泰尔,薇拉·巴克斯泰尔》对杜拉斯来说,是典型的自我纠正的一步棋。这部电影的主要情节来自她1968年的舞台剧《苏珊娜·安德勒》(Suza战争电影nna Andler),她后来觉得这出戏是一场 “商业赌博,充满尴尬的传统情节剧元素”。戏剧的情节以一段三角关系为核心。剧名中的人物苏珊娜是一位忠诚的妻子和尽职的母亲。她的丈夫外遇不断,虽然他很会赚钱战争电影,但控制欲很强。她坐在将来要租下的豪华别墅里,这笔奢侈的消费要花去一百万法郎,剧中丈夫为她第一次外遇花的钱也是这个数字,那是她情人米歇尔·凯尔(德帕迪约饰)的安排。
戏剧通过这种不忠突出了夫妻之爱的消弭战争电影,暗示苏珊娜打算和她的情人一起离开,但是电影则把关注点放在了薇拉·巴克斯泰尔“恶魔般的忠诚”的后果上。
《巴克斯泰尔,薇拉·巴克斯泰尔》剧照
舞台剧和电影在结构上最大的区别在于,电影引入了第四个角色“无名战争电影氏”,她和薇拉·巴克斯泰尔(克劳迪恩·嘉贝饰)长时间对谈,从而把一出阴谋从戏剧性的危机事件转化成了关于妻子困境的口头讨论——通过这种策略性的间接化处理,转移了有原戏剧的情节剧元素。
间接的交谈、迟疑的话战争电影语以及隐晦的表演都和影片主旨相吻合:主人公回避她资产阶级生活中的重大崩溃。就像杜拉斯在谈薇拉·巴克斯泰尔的被动地位和对婚姻的付出时所写的,“行动时,她好似绕过自身,(避开了)自己的身体”。
《巴克斯泰尔战争电影,薇拉·巴克斯泰尔》剧照
这种悬浮的气质决定了影片的美学风格。薇拉·巴克斯泰尔独坐在空荡荡的房子里,不断有电话打进来,起初没有人接,这些电话不时打断影片,使全片弥漫着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惊恐感。杜拉斯在拍室战争电影内戏剧场景时切了很多大海和其他户外空间的远景镜头,在这些镜头里,演员突然进入了停顿状态,就像突然停在半路上,或者慢慢挪动步子,仿佛预感到灾难来临。
《巴克斯泰尔,薇拉·巴克斯泰尔》剧照
然而,这些对话概括战争电影了有关巴克斯泰尔夫妇关系的事实,暗示最坏的结果:薇拉·巴克斯泰尔会在别墅里自杀?可能已经发生了。最冗长、最令人费解的对话都发生在薇拉·巴克斯泰尔和来看望她的女人们之间:首先是她丈夫之前的一个情人(诺艾战争电影尔·夏特勒饰),然后是塞里格饰演的“无名氏”,她不请自来,一直向薇拉·巴克斯泰尔作为妻子、母亲、情人的生活发问,好像是有意在帮巴克斯泰尔找到自己的身份。
《巴克斯泰尔,薇拉·巴克斯泰尔》剧照
“无名氏”和战争电影薇拉·巴克斯泰尔之间发生了紧张的化学反应,杜拉斯承认,把“无名氏”设置成女性是一个败笔。她在一个采访中说过要重新写一个剧本来修正,她解释道,如果这个陌生人是一个男人,那他来访的原因是被薇拉·巴克斯泰尔战争电影的名字吸引,这就和欲望有关。相反,“受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杜拉斯选择了女性的形象,无意识中在两人间造成了一种敌意。她会说:“如果不行,只是因为我对此不感兴趣。”
《巴克斯泰尔,薇拉·巴克斯泰尔》剧照
饰战争电影演这个身份特殊的“无名氏”的是欧洲艺术电影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星之一——著名女性主义活动家,1975年的杰作《让娜·迪尔曼》的女主角德菲因·塞里格——杜拉斯把最珍贵的台词都给了这个角色,包括她经常用来说明战争电影女性如何从沉默寡言中生出力量的一句话:
“女巫也是这样来的。在中世纪,男人们都在外打仗,参与十字军东征,乡村妇女们被抛下,独自一人,与世隔绝,整月整月地呆在森林小屋里……正是在这种孤独中,她们开始同树木战争电影、植物交谈,从自然中创生智慧。但她们被当作女巫,被烧死。”这句话出自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被学术界誉为“法国史学之父”,代表作有《论人民》《女巫》)1862战争电影年的史学著作《女巫》,杜拉斯在后面加上了半句,“其中有一位,叫薇拉·巴克斯泰尔。”
《巴克斯泰尔,薇拉·巴克斯泰尔》剧照
七十年代初,杜拉斯认同于一种破坏性的、差异化的女性主义,也就是格扎维埃·高杰(Xa战争电影vière Gauthier,笔名Mireille Boulaire,法国作家,记者,女性主义学者,创办了《女巫,女性生活》杂志,这是一本聚焦于妇女斗争的艺术与文学评论杂志)创办的刊物《女巫》(Sor战争电影cières)提出的那种女性主义,杜拉斯也参与了该杂志的命名。塞里格这段关于女性被抑止的语言的旁白,让这个人物变成了杜拉斯的代言人。
因为提到薇拉·巴克斯泰尔和她丈夫时都是叫全名,所以“巴克斯泰尔”就成战争电影为影片中除了达雷西欧的配乐之外存在感最高的声音。达雷西欧的配乐主要由安第斯琴声构成,在整部影片中此起彼伏,像是随一阵阵风涌现。这段音乐略带异教色彩,影片对它的解释是说它来自森林边上外国人开的派对,是一战争电影种“外部干扰”。音乐和姓名是杜拉斯诗性表达的关键部分。荒谬的婚姻仪式一直持续,没有定数的威胁山雨欲来,在《巴克斯泰尔,薇拉·巴克斯泰尔》中,这二者抽象地融合在一起,并随着达雷西欧绵延不绝的旋律节拍荡漾战争电影开来。
《巴克斯泰尔,薇拉·巴克斯泰尔》剧照
影片结尾,“无名氏”和薇拉·巴克斯泰尔结束了无穷无尽的谈话,在被玻璃封死的别墅中漫步,这段对话呼应着巴克斯泰尔夫妇之间精疲力竭的关系。就像被施了魔法似的,她们战争电影仿佛正在涉过一段粘稠的虚空。杜拉斯让一位饱受摧残的中产阶级女跳了一段芭蕾,但又用达雷西欧的伴奏堵住了她对婚姻中逆来顺受的控诉。
《巴克斯泰尔,薇拉·巴克斯泰尔》剧照
很多人在听“印度之歌蓝调“时会误以为这战争电影是三十年代的曲子——无论是虚构人物还是我们都会这样认为——觉得它不像是某人专门为影片创作的。同样,一直威胁着薇拉·巴克斯泰尔苦闷生活的外部音乐也像是现成的曲子。这就是达雷西欧独特配乐的天才之处。这两首战争电影曲子在影片的结构上都有明确的功能,塞里格在两部影片中也进行了截然不同的表演,这都表明了杜拉斯在创造幻境、表达混乱时有着无边无际的魔力。
《巴克斯泰尔,薇拉·巴克斯泰尔》剧照
- FIN -
真的有必要拍那么多大屠杀电影吗?
珍惜这样的院线片
沉寂20年的亚洲大导演,真的翻身了吗?
据说这是中国战争电影文艺青年最爱的导演…
从日本电影的年度十佳到奥斯卡大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