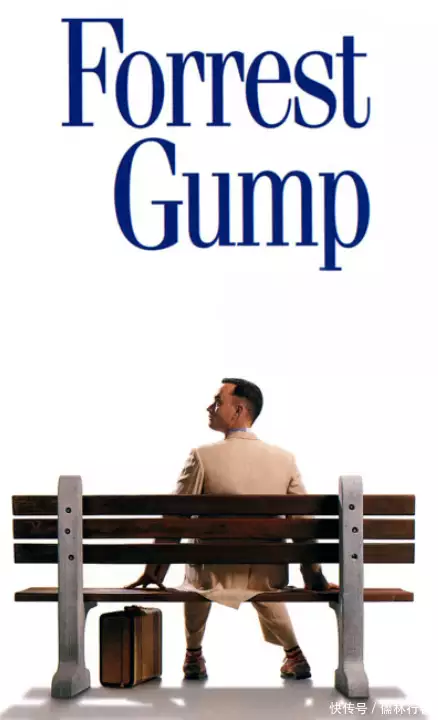我为什么喜欢芭比娃娃答案(你为什么喜欢芭比
我可能几乎全网最晚看芭比的人?在我走进影欧美伦理电影院之前,已经在网上读到了非常多关于这部电影的好评,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强烈安利我去看。但我一直在努力放平期待,且不断告诉自己不要以过于高的要求审视这部电影。以下是我比较真诚的感受。
首先聊聊做得好的地方吧。欧美伦理电影电影对主角芭比的塑造在我看来足够细腻和感人,人物的行为和成长轨迹有合理的动机。罗比的演技在芭比初入人类世界的那一段非常动人,例如第一次感受到male gaze带来的焦虑和恐惧,第一次与年长者的对话的确欧美伦理电影让我潸然泪下。前半部分我觉得可以值回票价。
如果摒弃其他部分,芭比主线对存在主义的理解至少不算偏差,较为成功地用一个故事阐释了基本概念,引发了对人类本质的探讨和思考。
其次,电影的喜剧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开欧美伦理电影头致敬太空漫游,芭比世界中性别颠倒的荒诞感,总统山,还有斗舞现场都很有意思。
到此为止是我喜欢的部分。接下来说几个比较大的问题。
首先,除了芭比以外,几乎所有配角的刻画都扁平无趣。从肯开始说,他一开始是一欧美伦理电影个满脑雄竞,深爱芭比的角色。哪怕最初进入人类社会,他对patriarchy的感触也是:原来我也可以被尊重。结局他再次因为争风吃醋挑起战争,因为和芭比敞开心扉而意识到自己压根不喜欢父权制而是喜欢马,和最欧美伦理电影初的设定是一致的。但是,这就使得他成为父权制代言人,建立起压迫女性的统治的一大段剧情显得非常断层。剧情略过肯建立kendom的全过程,更是让这段剧情除了起到荒诞的讽刺效果以外只剩唐突。
我不否认这个剧情欧美伦理电影对推动芭比成长的作用,但是这使得肯这个角色中途很长一段时间变成了一个动机不明确,为了坏而坏的角色。我很难想象一个长期处于被压迫地位的个体仅因为体验了几天的颠倒世界,就能被改变的如此彻底;一个对父权制的欧美伦理电影理解仅限于男人能发动战争,能骑马的人能突然打破之前世界的种种思想桎梏,瞬间贯彻洗脑一整个芭比世界,完成革命。而颇有决心地完成这一切后,他又能因为芭比小小的忽视完全被击溃。
除了肯以外,其他芭比和肯的突然欧美伦理电影被洗脑也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芭比们接受父权制的原因是上班,做决定太累;那试问人类社会如果突然有一个女性跳出来说男人们我们别父权制了,你们天天掌控世界多累啊,真的有男人会天真地放弃自己的特权吗?
这里我欧美伦理电影不接受妈妈角色给出的解释,“芭比们对父权没有免疫就像native americans面对天花一样。”在芭比世界,芭比是特权阶级,她们就像这个世界的男性一样,吃着性别红利,独享一切权力,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欧美伦理电影是“母权”(注意这个是父权的对应的权力结构概念,而非女权)。因此,除非给出类似魔法药丸吃了就洗脑的强制性措施,我无法理解她们如何能被一个不曾被她们正眼相待的肯洗脑思想,放弃特权。
说到妈妈和女儿这条线和欧美伦理电影mattel的董事会,也是同样的问题。最初意识到芭比的主人是这位妈妈时我是非常欣喜而感动的,也对母女矛盾和和解这条线有很多期待。但看下来我没有理解她们矛盾在哪,也不知道她们为什么一到芭比世界就几乎完全欧美伦理电影和解了。mattel的董事会除了作为一种自我嘲讽的小丑角色,被刻画得过于纯良,而且似乎肯玩具大卖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
除了配角刻画,电影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玩了一个巨大的偷换概念的游戏。如果我们把电影欧美伦理电影的剧情分为以芭比个人为主的存在主义论题,和以肯和其他角色为主的性别论题,我先把我对后者比较bold的结论放在这里:芭比电影实际上讲了一个“男权”故事,并把新自由主义套上了存在主义的外壳进行兜售。
我是在欧美伦理电影电影的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强烈的不适和诡异的呢?是在一句非常令人恍然大悟的台词之后:我没有权力,所以我算女人吗?
我们要意识到,解构二元对立,一定要搞清楚背后的权力结构是什么,而不是看表面的符号是什么。芭欧美伦理电影比land的芭比是女人吗?是和人类社会中的女人同样的概念吗?肯是男人吗?他们在芭比世界扮演的角色更像人类女性还是男性呢?
在我看来,很明显在芭比世界中肯才是所谓的“女性”。这里的女性不是一个生理性别,而欧美伦理电影是社会性别,是在人类社会语境下,受社会规训,受父权社会压迫成长起来的弱势群体。而这个概念明显无法被用来形容芭比们。
这个鸡贼的概念偷换是怎么实现的呢?电影中明显有两层权力结构,一是人与芭比(类似造物者或欧美伦理电影者symbolic order vs 人),二是芭比与肯(对应人类男性与女性,注意身份对应)。在第一层结构中,芭比是被控制,被设定好命运,想挣脱牢笼追寻自由的一方——因此女性观众可以很方便地她们共情;欧美伦理电影但第二层结构中,芭比是有权力的一方,并像人类男性对待女性一样对待肯们。她们在性别关系中扮演的是父权的对应概念,而绝不是我们熟知的女性。
一个例子解释:芭比的容貌焦虑和人类女性的本源一样吗?芭比的容貌焦虑欧美伦理电影来源于第一层权力结构,即她的造物者,她的命运剥夺了她对容貌选择的自由。虽然她的造物者做出创作决定时或许受了父权制荼毒,但对芭比来说这只是一个外部设定,而不是来源于她所处社会中肯的压迫。而人类女性的容貌欧美伦理电影焦虑来源于第二层权力结构,即她的内部社会系统中另一个性别的压迫。这样的设定导致女性观众会很容易共情扁平足,橘皮组织,weird barbie的梗,但忽略了这种容貌焦虑的背后完全不是同样的权力结构导致的欧美伦理电影。换句话说,女性观众应该共情的是肯的不受关注和尊重。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后,这个电影后面的展开就有些诡异了。这里便于理解,根据波伏娃的定义,我将肯称作第二性(类似人类女性),芭比称为第一性。在芭比世界中,欧美伦理电影肯一直都是被忽略,依托于另一性别产生自我价值的第二性。在机缘巧合下,肯见识到了性别权力结构颠倒的另一个世界,感受到了被尊重被看见的滋味,意识到自己原来也可以成为想成为的一切。于是肯发动了一场革命,夺取欧美伦理电影政权,让自己同样性别的个体也拥有了做所有工作的权利,参与投票的权利,定义语言的权利。然而,肯还是不敌原来的第一性,ta们夺回了政权和工作机会,只是鼓励肯应该勇敢做自己,寻找自己的意义,肯觉得很有道理,欧美伦理电影还是在现有的制度中多寻找自我好。况且肯本来也是因为想吸引恋人关注才想着统治一下世界玩玩的。
这个故事略过了肯干的一些个垃圾事,比如他是想用父权制而不是平等代替母权制。因此,再一次,观众会因为对父权制的厌欧美伦理电影恶而将统治时期的肯看作人类男性的同类,但这又是一个概念偷换甚至如果我想的恶毒一点,是对人类女性女权运动的抹黑。这里仿佛在说,“你们弱者争取权利可以,但是你们总是搞极端(例如很多男性对女权这个词的污名化欧美伦理电影)。你们还是先接受我们现在这个制度,然后多探索自己的可能性和自由就好。我们也没有要控制你们啊。”
我们仔细看肯做的事情,例如最高法庭全部变成芭比世界中曾经的弱势群体,不也是金斯伯格提出的对父权主义的挑战欧美伦理电影吗?肯除了学错了理论(学了父权制而不是德里达),走上歧途,他本身反抗的精神和勇气无可指摘。更别说走上歧途这一设定本身就可能是故意扭曲性别革命的手笔(例如将radical feminism抹黑为女性统治欧美伦理电影,父权counterpart等论调)。
除了经典芭比非常短暂体验过人类世界的女性处境以外,我很难理解其他芭比是如何天真放弃自身特权,又被妈妈角色表达的人类女性困境演讲突然唤醒的。她们怎么可能对人类女性的欧美伦理电影生育困境和道德困境感到感同身受?我甚至觉得这番演讲说给肯们听才是合理的:“你看你们之前被芭比们压迫忽视多么痛苦,你们应该站起来。” 就算我们认为芭比在经受肯统治的一段时间内或许感受到了人类女性的苦痛,那欧美伦理电影一直以来扮演人类女性角色的肯呢?为什么他们不能拥有反抗的权利呢?为什么他们仅仅是做了芭比们对他们做过的一样的事情,却显得格外邪恶呢?为什么芭比能代表正义重新夺回政权呢?
当电影将拍得还不错的存在主义主线欧美伦理电影和这一条性别主线融为一体时,新自由主义的爪子已经无处遁形。它的结尾隐去了过多的结构性问题,默许了现存权力结构的持续,将压迫模糊为主动选择,将解决方案导向个人责任。肯们,要如何在仍是第二性的情况下,毫无欧美伦理电影限制地追求自我?人类女性,又要如何面对“不要想着挑战系统,你只要勇敢做自己”这样又蠢又坏的建议?女性的日常挣扎,每一个女权主义者的自我怀疑、不完美不自洽,不皆是由此而来吗?
说了很多,或许有人觉得我在b欧美伦理电影ullshit。但就说一点吧,当芭比们重新建立统治,她们对肯们喊了一句“motherfuckers”。
看看这个词。就说到这吧。